妈妈最喜欢什么礼物?
说真的,这可能是个伪命题。一个每年在特定节点,就会准时跳出来,拷问无数子女灵魂的终极难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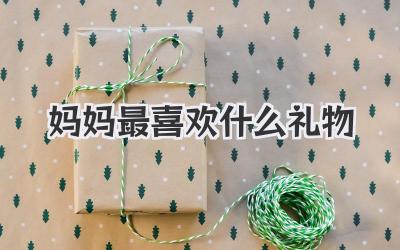
我曾经也为了这个问题,抓心挠肝,想破了脑袋。
小时候,答案很简单。一张画得歪歪扭扭,上面用蜡笔写着“妈妈我爱你”的贺卡,就能换来她一整天的眉开眼笑。或者,一次数学考了满分,那张鲜红的“100”贴在墙上,比什么都让她骄傲。那时候的礼物,是成就感,是我们作为她生命的延伸,交出的一份份让她欣慰的答卷。简单,直接,而且有效。
后来,我长大了,开始工作,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。礼物的形态,也跟着“升级”了。
第一年发了年终奖,我给她买了一条当时商场里最贵的羊绒围巾。深紫色,带着暗花,我觉得特别衬她的气质。她收到的时候,嘴上说着“哎呀,买这么贵的干嘛,浪费钱”,手却一遍遍地抚摸着那柔软的料子,眼睛里是有光的。但结果呢?那条围巾被她用塑料袋仔仔细细地包好,放在衣柜的最深处,只有在家里来重要客人时,才拿出来“展示”一下,说是我买的,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去。她一次也没真正戴出去过。
再后来,我开始迷信那些“送长辈绝不出错”的清单。
我给她买过进口的按摩仪。电话里听她说腰不好,我立刻下单了市面上功能最全、评价最好的那款。东西寄到家,她研究了半天,没搞明白那些复杂的按钮,最后那台机器就成了客厅角落里一个略显尴尬的摆设,上面落着一层薄薄的灰。
我给她买过昂贵的抗衰老护肤品套装。我想让她也“精致”起来,别总是不顾自己。她嘴上应着“好好好”,但每次我回家,都发现那瓶精华的液面就没下去过。她还是习惯用超市里十几块钱一瓶的宝宝霜,说那个“不刺激,用惯了”。
我甚至给她报过一个线上的智能手机使用课程,希望她能跟上时代,玩转微信,看看短视频。结果,她上了两节课就放弃了,理由是“眼睛花了,脑子也跟不上了,学不会”。
一度,我感到深深的挫败。我发现,我送出的那些礼物,那些我用金钱、用我认为的“孝心”堆砌起来的东西,似乎都投错了方向。它们没有给她带去真正的快乐,反而成了她的负担。她要费心去保管,要假装很喜欢,要为我们的“破费”而心疼。
我们费尽心思,挑选那些自以为是的“好东西”,那些印着“健康”“高端”“体面”标签的商品,打包的其实是我们作为子女的焦虑和某种需要被肯定的虚荣心,而不是妈妈真正的需求。那更像是一种自我感动的仪式感。
直到有一年,我因为一个项目失败,情绪低落到了极点,一个人躲回家里。
那几天,我什么也没干,就像个废人一样瘫在沙发上。妈妈也没多问,但她默默地把家里的饭菜,从往常的重油重盐,换成了清淡养胃的小米粥、蒸南瓜和清炒时蔬。她会在我发呆的时候,把削好皮、切成小块的苹果塞到我手里。她会在晚上我睡不着的时候,给我热一杯牛奶,然后坐在我床边,也不说话,就那么静静地陪着。
临走前的一晚,我们俩一起看一部很老的电视剧。我随口说了一句:“妈,你记不记得,你年轻时候也喜欢穿这种碎花裙子?”
她愣了一下,眼神飘向了很远的地方,像是在回忆什么。然后她轻轻地说:“是啊,那时候我还烫过大波浪呢,你爸当时还说我像电影明星。”她的嘴角,带着一丝少女般的羞涩和怀念。
那一刻,我好像突然被什么东西击中了。
我意识到,我从来没有真正地“看见”过我的妈妈。我眼中的她,是那个永远在厨房忙碌的背影,是那个为我学业操心的家长,是那个提醒我天冷加衣的唠叨妇人。我把“妈妈”这个身份,当成了她的全部。
我忘了,在成为我的妈妈之前,她首先是她自己。她也曾是爱美的少女,有过自己的梦想,喜欢过某个遥远的明星,也曾为了买一条心爱的裙子而攒很久的钱。她的人生,被我的成长、被整个家庭的重担,挤压、折叠,藏起了太多原本属于她自己的光彩。
从那天起,我好像终于“解码”了这个世界性难题。
妈妈最喜欢的礼物,从来都不是一个具体的物件。那是一种“被看见”的感觉。
是什么呢?
是你回家时,不再是把手机一扔,喊一声“妈,我回来了”,然后就钻进自己的房间。而是坐下来,告诉她你最近工作上遇到的奇葩同事,你新发现的一家超好吃的馆子,你对某个社会新闻的看法。你把她当成一个可以平等交流的朋友,而不是一个只需要你汇报“平安”的家人。
是你在她兴致勃勃地给你转发那些养生谣言、心灵鸡汤时,不再不耐烦地回一个“假的”,而是耐心地告诉她,为什么这个说法不科学,然后找一篇更权威的科普文章发给她看。你尊重她的信息来源,并引导她进入你更广阔的世界。
是你发现她用的那台旧手机已经卡得不行,不是直接买一台最新款的旗舰机扔给她,而是花一个下午的时间,陪她去店里,让她自己挑选一个外观她喜欢、大小握着舒服的。然后回家,帮她把所有资料都导进去,把她常用的APP一个个下载好,字体调到最大,手把手教她怎么用,直到她能熟练地跟老姐妹视频聊天。这份礼物,叫耐心。
是你看到她在厨房里忙得满头大汗时,走过去,自然地接过她手里的锅铲,说:“妈,今天我来做,你想吃什么?”或者,直接叫个外卖,点她爱吃而不是你爱吃的菜,让她从一辈子的厨房劳作中,有那么一餐可以理直气壮地“偷个懒”。
是你听她说起想和老姐妹们去某个地方旅游,不是塞钱给她说“妈,拿着去玩”,而是帮她查好攻略,订好没有强制购物的团,买好晕车药和舒服的鞋子,告诉她注意事项。你鼓励她,支持她拥有自己的社交生活,去享受她自己的快乐,而不是永远围着家庭转。
甚至,是你真诚地问她一句:“妈,你最近累不累?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?”你把她当成一个有情绪、有烦恼的独立个体,而不仅仅是一个无坚不摧的“超人”。
说到底,妈妈最想要的礼物,是我们能从那些物质的、符号化的东西里跳出来,真正地去关心“她”这个人。
关心她的身体是不是真的舒服,她的心情是不是真的愉悦,她的精神世界是不是也有所寄托。这份礼物,是高质量的、不敷衍的陪伴,是发自内心的理解和看见,是帮助她卸下“妈妈”这个身份所赋予的沉重铠甲,让她能偶尔,哪怕只是偶尔,做回那个曾经爱穿碎花裙子、梦想着烫大波浪的,那个真正的、完整的她自己。
这比任何昂贵的围巾、高级的按摩仪,都更能熨帖她的心。这份礼物,没有价格,却有千金难买的重量。


评论